这届年轻人,是最孤独的一代吗?
共
4459字,需浏览
9分钟
·
2021-10-28 02:44

国庆过后,郑州突然冷了起来,不下雨的时候也总是雾蒙蒙的。周末傍晚,小玉从厨房柜子的最里侧拿出一个日式小炉子和一个奶白色的小锅。倒上水加入火锅底料,还有事先切好的香菇、杏鲍菇、金针菇。小小的火起了,待整个汤汁咕嘟咕嘟,就可以涮自己爱吃的食材了。背靠沙发坐在地毯上,顺手开一听啤酒,圆滚滚的猫咪在脚边睡觉。此时,她可以不用理会工作群中的消息。从柔和清淡的一口啤酒开始,到厨房中哗哗流水声结束,一切糟心事儿在过程中烟消云散。今年,是小玉独居的第二年。两年的独居生活不是每天都如这样平静且美好,当意外发生时,她也常常觉得孤立无援。美国作家梅·萨藤在《独居日记》里这样描写独居生活,“只有当我独处,环视这屋子,重温旧时和它的对话,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这种“生活的滋味”混合着独居青年们的独立与孤独、自尊与自洽。小玉理解中的独居生活,是“自由与孤单的并存”,是“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的混合体”。独居,是年轻人生活的一个阶段,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憧憬的居住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或许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答案。“独居,更像是一个靠近自己的过程。”小玉所说的这个“自己”,是那个你可能还未发现的、真实的自己。小玉是独生女,大学之前没离开过父母,大学之后住在宿舍,从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居。毕业后她顶着房租压力,在郑州老城区租了一间单身公寓,房间不大,30平的样子,客厅和床挨在一起,还有个朝南的小阳台,和一个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家里阳台采光很好,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帘拉开;小玉还买了很多漂亮的餐具和杯子,每天认真做饭,经常为“用哪个盘子盛食物”这个问题而纠结很久;她还添置了一台落地灯、一个书架,上面放了127本书。一个人住的大部分时候,日子平淡且自由,但孤独感不时来袭,小玉发现了那个“低能量”的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孤单,是一个平常的、重复了很多次的下班晚上。“冬天天黑得早,打开门屋里漆黑,静悄悄的,只有楼下小孩子们偶尔的嬉闹声。”那天晚上,小玉没有自己做饭,早早洗漱后躺在床上,试图用看剧缓解孤独感。那之后,她常常需要傍晚时分与孤独情绪作抵抗,小玉说,“毕业后才知道原来自由和孤单是并存的,独处也需要能量。”七七出现在下班回家必经的路上,小玉没有犹豫,轻松把它拎起来带回了家,此后家里有了个等她回家的“小东西”。但七七却成了生活里的“突发事件”。周末下午有快递送上门,开门的间隙,七七从屋里窜了出去,慢悠悠地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小玉想都没想,出门追猫了。结果阳台窗户大开,空气对流,没等小玉走几步,大门“砰”的一声锁上了,猫也顺着楼道跑的不见踪影。“完了,钥匙和手机都在家里”,小玉心想,“还是得先把七七抓回来。”12层楼,她来来回回爬了5遍也没找到那只猫。又回不去家,只能踢着拖鞋向物业求助,叫来开锁师傅。几经折腾,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小玉还是放心不下七七,又拿上钥匙出门寻找,终于在7层和自己家同样位置的住户门口,发现了蹲在一旁的七七。从那以后,小玉逐渐与孤独感和解,她说,“孤独感和意外是独居的一部分,每种感觉都是阶段性的,情绪来来去去,顺着它就行了。”阿宁的生活比一般独居者更加自由,因为她不仅独居,还是自由撰稿人。看看她现在井然有序的生活,真不敢相信她之前的日子过得一团糟。阿宁说,“刚开始写稿那会儿,我真是高估了我的自律能力。”家里全是速食产品,要不就是点外卖;一两个星期也不想拖一次地;经常一边焦虑一边拖稿……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约束的状态,带来的往往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因失去秩序感而变得颓废的漩涡。这种日子过了半年,阿宁实在有些崩溃,“再不好好写稿,房租都要交不起了。”好的生活状态往往只需要从一次大扫除开始,丢掉过期的食物和速食产品,收拾好沙发上乱七八糟的衣服,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好心情就这么回来了,阿宁决心找回生活的秩序。她开始把工作细化到每天的每个小时,自己动手做晚餐,每三天收拾一次屋子。阿宁明确了一件事,选择自由,你需要比平常人更用心地做时间管理,缺乏意志力的人会在自由生活中成为一名“废柴”。“独居者的仪式感”和“自由职业者寻找秩序感”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可能需要为了独居的可持续性而付出点什么。像阿宁和小玉这样的独居青年不在少数,去年国家民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高达2.6亿,超过英、法、德三国人口总数,其中8000万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上升至9200万。但是现在,关于独居青年的定义其实还没有完全理清。到底是一个人住一套房算独居,还是几个人合租一套房也算独居?在欧美国家,不少关于独居的研究都指的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套房,但中国的研究却主要针对“空巢青年”,即离开父母居住,无论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合租,或者与情侣同居都算进“空巢青年”的范畴。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风笑天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却表示,自己不太赞同“空巢青年”这个概念。实际上,“空巢”一词来源于“空巢老人”,而“空巢老人”指的是孩子离家后,留下老年父母独自在家,这种被动的状态并不适用于独居青年。风笑天认为,“独居”应该是一人户,进门后不需要跟任何人互动来往,才能称作独居。国内排除几个人合租一套房的情况,真正的独居少之又少。这样说来,现在并没有看到中国独居青年数量越来越多的证据,关于独居青年的数量似乎有待考究。风笑天说,“应该明确的是,人口是按照户口进行统计的,独居数据不仅仅针对青年人口,而是包含了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所以一人户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独居青年数量的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独居青年的状态的确会长期存在,独居始终是自主选择与被动接受的混合体。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和单位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单位通常会给员工提供住处。而经济体制改革后,工作单位不再提供集体宿舍,所以工作时间外的住宿问题全权由年轻人自行解决。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租房成为必然。为避免相互打扰,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群便会选择独居,所以早期的独居是一种具有经济实力基础下的选择。随着一届又一届毕业生涌入社会,独居青年便成为了一个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的文化。在欧美国家,独居文化则来得更早一些。在美国,2015年时就有超过50%的人处于单身,独居人口占美国总户籍的28%,独居者成为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关于众多美国人选择独居的原因,或许能从2013年,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撰写的《单身社会》中找到答案。他在书的结尾写道,“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网、超级活跃、24小时无休止的社会文化中,……独居带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在他看来,现如今有更多人选择独居,是因为他们能够负担这种生活,这代表着更好的生活品质,更独立的思想,以及更优质的教育水平。而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三联生活周刊》曾指出,目前中国在不断享受个体自由的同时,还需要需要面对传统单位制和其代表的传统国家福利制度的结束,以及对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换句话说,在上一代人还享受着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和单位分房的稳定生活的时候,后一代人就生活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中,同时需要面对并适应更换工作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以及人际关系的短暂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王怡丹在《城市独居青年的个体化研究》的研究结论中也指出,社会个体的确经历了从“总体性社会”到“个体化社会”的结构之变。这种转变,也带来了青年人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观念之变。随之而来的是青年人自我认同感的上升,和自我牺牲感的降低。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独居现象也与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有关。个人主义上升、婚姻推迟、生育率下降,以及同居率和离婚率上升都使得单身人口增加,而单身与独居有着强关联性。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也为青年人搭建了一个身体“缺席”也能交流的“缺场空间”实时技术压缩了时间距离,使社会关系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在场”与“缺场”的并存,极大地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紧跟独居文化而来的是“一人经济”热潮,2016年左右已有一人食餐厅、自热食品等主打单身青年的产品;RIO也推出微醺系列,有了“一个人的小酒”的slogan,宠物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在众多人的印象中,“独居”往往与“孤僻”、“冷漠”等词汇联系起来,但是克里南伯格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他采访的300多名独居人的故事里,大多充满自由的气息,他们的确是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但同时与已婚者相比,这些独居的人更愿意与朋友和邻居来往,也更愿意前往公共空间与陌生人交流,这些结果证明了很多传统观念是错误的。同时,青年独居也不意味着更难寻找伴侣或者晚婚,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风笑天也指出,不能认为独居青年是弱势群体,更不能默认为这是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人们之所以追求独居,是因为独居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当今社会最神圣的现代价值观,但很少有人想永远独居,这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是一种开始一段关系前或者结束一段关系后的可靠选择。那么年轻人到底需要怎样的住所?也许不是合租,也不是独居,而是共居(co-living)。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尽管当代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距离,但是距离太近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距离太远人与人之间必要接触则会消失殆尽。独居了3年的森洋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这三年前后搬家四次,从一开始的找舒适的房子,到后来希望找到与七八个好友,距离两三公里远的房子。他说,“这样不会相互打扰,当然日常的相聚也不会让我觉得太孤单。”这种理念在瑞典早已盛行。上世纪30年代,瑞典人就意识到,独居的人希望与周围的人保持联系。所以从那时起瑞典规划师就开始构思集体住宅,住宅二楼有一个公共自助餐厅,人们可以和邻居一起吃饭,如若不想也可以在房间内下单。国内也出现了类似“共居”的创意。比如上海、广州的706生活实验室尝试了一场关于“共享社区”的居住生活实验。在保证租客单独居住质量的前提下,设计了很多活动和规则,来重新有意识的构建真实地对话和真实的交往关系。与之类似的还有北京的地瓜社区,将原来的地下居委会活动室改造成社区中心,让年轻人在独居的过程中,保有邻里间正常的舒适的社交。这种相互依存的生活状态,正在使真正的独立成为可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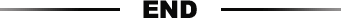
点赞
评论
收藏
分享

手机扫一扫分享
举报
点赞
评论
收藏
分享

手机扫一扫分享
举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