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意义:推动数字时代变革的“无形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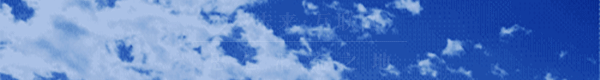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数字文明日益占据主导,有三种典型现象:人机交互手段日趋丰富,数字设备保有量大幅提升、使用频率显著增加,社会民众数字素养提升。电子游戏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了以上所有三种变化。
如今,在算法时代,面对备受大众关注的算法治理问题,游戏依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个体用户与游戏开发者制定的代码规则间的复杂互动,为探索算法治理难题提供了概念与实践工具。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考虑游戏的定位,在尊重游戏权的同时,探索游戏从作为监管对象向作为治理手段的转变。
腾云特约作者[1]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职业法律博士(J.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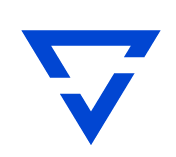
20世纪中叶以来的信息革命,引起了由数字文明主导的当代社会:一方面,数字设备与日常生活的交互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对数字设备的保有与使用,成为日常生活愈发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素养教育框架的建设,亦已提上日程。[2]
从笨重罕见的初代计算机“埃尼亚克”(ENIAC),到轻盈普遍的智能手机,电子游戏(以下或简称游戏)在数字文明开端与兴盛过程中的作用,却长期遭到忽视。现有的发展理念和监管思路,也更多将游戏作为监管对象,却没有为游戏留下太多其它可能。
基于对计算机发展史的梳理,我希望提出一个观点:在回顾游戏如何影响数字文明进程的同时,有必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考虑游戏的定位。
在本文中,我将遵从这样的顺序对该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以井字棋、战棋与星际战机等典例,概述早期游戏的发展;
其次,就数字设备与人的交互,游戏推动了“画板”、虚拟现实与操作系统等“里程碑”的诞生;
再次,在数字设备的保有量的问题上,如上村雅之(Masayuki Uemura)所述,在“个人计算机实际上什么也做不到”的年代里,在世界多个地方,游戏推动了计算机的普及[3];
同时需要注意,对游戏的破解、修改与再创作,同样是各地数字文化诞生的“摇篮”;
最后,我希望讨论,在制度层面,游戏权的证立与保护,并希望简述游戏作为数字社会治理手段的可行性。

01
意想不到的开端

电子游戏的诞生,没有比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晚太多。但彼时,没有人会想到它会在未来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埃尼亚克”诞生后不到5年,潜心钻研人机交互的剑桥大学博士生桑迪·道格拉斯(Sandy Douglas),便成功地将“井字棋”移植到了计算机上:通过类似电话按键的输入设备,用户可以选择“人先行”或“计算机先行”;根据规则,用户与计算机轮流在屏幕所示“3*3”网格中画“X”或“O”,先将三种同一图案连成一线者,获胜。[4]
这是游戏的开端之一。随后,跳棋与桌球也纷纷有了计算机版本。[5]
相比以研究为导向的趣味游戏移植,利用计算机运行战棋游戏的现实价值,其实更加显著。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海军着手研发计算机战棋。[6]直至50年代中期,当时的计算机性能,才足以支持其设想:一款耗资1000万美元、可以实时模拟48艘舰船航行、(反)侦察与战斗的战棋。[7]
美国陆军与空军几乎同时跟进,开发与危机模拟、核战争、全球战争相关的各类计算机战棋。[8]计算机战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陆军后续的作战训练方式。
1980年,从越南战争上不甚成功的、以大量传感器打造“电子战场”的设想出发,美国陆军建立数字战场实验室:通过大量传感器,建立“准确、完整、实时”的实训对抗记录,并以计算机战棋复盘、评议对抗细节。[9]
战棋的另一个影响是,如美国陆军情报、电子战和传感器项目执行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总结:计算机战棋的应用,让军方与爱好者社区都逐渐注意到了显示设备和其它交互手段的重要性。[10]
20世纪6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名计算机爱好者,开发了影响至为深远的《太空飞船!(Spacewar!)》。面对中央恒星的引力,“玩家”可操控两架太空飞船彼此追逐、闪躲、射击,击中对方者取得胜利。[11]

20世纪70年代初,《太空飞船!》传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
可以说,在《太空飞船!》流行以前,极少数人才知晓电子游戏;而在那之后,“想要观看游戏的人,足以挤满一整个体育场,这显得不同寻常。”[12]
这也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广泛流行的游戏。年轻的程序员们喜欢这款游戏,这首先让他们看起来非常极客:“沉迷技术、有种反文化意义上的酷劲”;这同时也成为发展个人化、交互式数字技术的路径之一。[13]
游戏的历史意义之一自此终于显现:因为游戏的意外诞生,个体与数字设备交互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02
游戏与人机交互的发展

恰如生于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已然习惯一切屏幕皆可触碰,当代社会里的大部分个体,也会将鼠标、手柄或其它操纵屏幕的设备视为理所当然。但就在数十年前,这还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有人因此获得图灵奖。
人机交互发生如此根本性变革的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那个正沉迷于《太空飞船!》的地方。
1960至1963年间,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太空飞船!》的操纵方式已较10年前的井字棋细腻不少:一个可以左右扭动的开关,控制飞船顺逆时针旋转;一个前后扭动的,控制速度的开关;一个“最好保持安静、不要让对手发现你正在击键”的开火键。[14]
游戏让萨瑟兰印象深刻,也启发了他“与计算机实时交互过程中的海量可能性”。[15]
萨瑟兰由此开发了“画板(Sketchpad)”:借助计算机配置的“光笔”,用户首次得以随意在屏幕上创建、绘制、联结或擦除所欲的形状。[16]这才是前述“理所当然”的开端。
萨瑟兰的妙思,也感召了鼠标的发明。[17]

此外,萨瑟兰还是“虚拟现实”设备的开创者。[18]
1965年,他发明了头戴式的实时显示设备、并开发了相应版本的《太空飞船!》。[19]因“画板等一系列对计算机图像领域先驱性、远见性的贡献”,萨瑟兰获授1988年图灵奖。[20]

同样痴迷于无垠星空的,还有操作系统的发明者肯·汤普森(Ken Thompson)。
1969年时,正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汤普森开发出《太空旅行》游戏:用户操纵飞船在太阳系内旅行,通过调节速度,飞船可以克服重力、在特定星球上降落。[21]然而,由于贝尔实验室调整机构和项目、停止购买高性能计算机,不久之后,汤普森被迫借用其它部门闲置的、“内存容量十分有限”的计算机。[22]
于是,为了继续遨游太空,无奈之下,汤普森在新电脑上重写了《太空旅行》。[23]
他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发、完善的工具,便是直至今日、仍有广泛应用的Unix操作系统。[24]因“对原生操作系统理论的发展,特别是Unix操作系统的实现”,汤普森获授1983年图灵奖。[25]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还和同年另一位得奖者丹尼斯·里奇(Dennis Ritchie)一道,将《太空飞船!》移植到了同一型号的闲置计算机上。[26]
屏幕交互和操作系统,远不是游戏所影响的全部。
如史密斯所述:计算机战棋中多个参与者同时观战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对分屏显示、视角切换、图形界面、设备联网、远程同步等技术的探索。[27]
20世纪70年代初期商业化的游戏手柄,塑造了个体日常“开关、运行、控制”其它类型数字设备的模式。[28]此外,在布拉德·迈尔斯(Brad Myers)对人机交互史的经典梳理中,游戏本身即与文本编辑、超文本、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并列为主要的交互应用。[29]由此可见,在数字设备与日常生活密切交互的开端处,游戏可谓二者间最重要的桥梁之一。
03
游戏推动计算机的大众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字文明叙事,背景通常坐落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大学校园。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计算机“进入寻常家”,各类数字设备的保有与使用,渐渐与日常生活难以分割。
在计算机的供给端,如前文所述,游戏推动了交互性的诞生;而在计算机的需求端,游戏同样是重要的解释因素。
恰如时人斯图亚特·德嫩伯格(Stewart Denenberg)的总结:“在向潜在用户推介计算机时,游戏是极具吸引力的特性。”[30]
甚至在冷战时期的美苏铁幕两侧,游戏的作用都难以忽视——
冷战铁幕的一侧,游戏培养了一整代数字文化的“乐之者”。
根据乔伊·朗金(Joy Rankin)的观察:20世纪60年代末,在首创大型计算机分时系统与BASIC语言的达特茅斯校园,变得“平易近人”的计算机,在学生间激发出“汹涌的创造力”。[31]通过联机版本的篮球、棒球、猜拳、回转滑雪等游戏,“计算机的感召……传遍“达特茅斯校园的学生。”[32]
在激发个体兴趣的同时,游戏亦成为联结数字世界新生一代的社会纽带:互助通关也好,互相嘲弄也罢,共同的游戏经历,让计算机与校园生活间,形成了“有形的、可见的”联系。[33]在数年后的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围绕现代互联网前身之一的PLATO平台[34],形成了合作氛围浓厚的网络社区。[35]社区成员们热爱游戏,但管理者的态度更加复杂。[36]
当然,在承认游戏的“教育、娱乐和其它价值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将游戏“斥之无用”或“必要之恶”的声音。[37]当时,社区用户的回应是:认为游戏没有那么有用的人,为什么不去读读詹姆斯·凯梅尼(James Kemeny,时任达特茅斯大学校长,参与开发了前述分时系统与BASIC语言)的经典《人与机器》呢?[38]
当个体面对数字世界时,游戏常常给他们第一印象。于是也不难理解,游戏如何在计算机早期被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意图销售尚属新奇的计算机的商家,至少有两种销售策略:一方面,如德里伯格回忆,“与学校管理层不同……现实中,不会不讲道理的商业世界,对游戏的看法截然相反”[39],新奇、有趣、象征技术狂热的游戏,是销售的“利器”;另一方面,商家亦努力将游戏与主流家庭价值观相挂钩:在广告中渲染全家共同游戏其乐融融的画面,以求提振销售。[4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英国,面向大众销售的计算机,必需图像和动画等“对游戏而言至关重要的功能”。[41]20世纪80年代初的澳大利亚[42]与新西兰[43]:玩游戏和写游戏,是个人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最后,在日本,不妨以上村雅之引言的后半句作结:“……有了红白机,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计算机什么也做不到,除了能玩游戏。”[44]
马丁·坎贝尔-凯莉(Martin Campbell-Kelly)对20世纪7、80年代之交的统计,是又一佐证:家用软件销售额中,约60%来自游戏。[45]
冷战铁幕的另一侧,游戏与计算机普及间的关联,依然紧密而广泛。
1980年代后半叶,捷克斯洛伐克的家用计算机保有量,迅速增长至约10万台[46];同期,绝大部分计算机的重要用途也是游戏[47]。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当时游戏同样有“社会纽带”的功效:在计算机俱乐部结识的个体相互拜访,乐此不疲地交换、讨论、联机游戏,既有游戏交易,也有频繁、深刻的社会交往。[48]
在邻近国家,相似的情况也在发生。
在捷克斯洛伐克游戏交易的来源地南斯拉夫,在“新近对计算机发生热情”的家庭的聚会上,大家纵情游戏,并炫耀新近购入的软件。[49]在波兰,建立、运营计算机俱乐部的动因是:“否则你只得坐火车,旅行很远,有时要到国境线上,去拷贝游戏”。[50]当然还有苏联: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游戏,很快在苏联掀起了类似的,玩耍、修改、再开发游戏的潮流;当地企业很快抓住了这一潮流,推出更为廉价、销路更广的计算机。[51]
因为有游戏,计算机从有用变得易用,又从易用变为常用。
04
游戏与数字素养的提升

无论数字设备有多易用、有多常用,数字文明的开端与兴盛,终究依赖于众多会用设备、擅用设备的个体。以计算机为例:只有在基本层面上先熟悉计算机的操作,才能在令机器为人所用的基础上,以至数字领域的创新。
我们可以说,游戏在将计算机带入千家万户的同时,也是早期那些“计算机小子”熟悉“笨重的箱子”的主要途径。
据梅拉妮·斯沃韦尔(Melanie Swalwell)总结:“用户从玩游戏中得到的愉悦和快乐……很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何20世纪80年代时,计算机风靡于非专家群体。”[52]
首先,是操作机器。在图形界面操作系统尚未普及的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打开电脑以后,基本上你就得开始编程”[53];另一方面,初学者还要“克服面对计算机的神秘感”,“避免乱按按钮,导致计算机崩溃”。[54]
因此,从熟悉、有趣且安全的游戏入手,便成最可靠的学习策略。适逢游戏杂志方兴未艾、刊登(小)游戏时常附带源码。于是,那些自己摸索的用户,常常这样写出人生中第一个程序:将代码一点点原样键入电脑,再惊喜地期待之后“魔法般的变化”。[55]
在有组织、成体系的计算机教育中,游戏同样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最早系统开展计算机教育的达特茅斯校园,时任校长凯梅尼不仅成功地打造了“以游戏为中心的计算机文化”,[56]还亲手开发了之后颇为风行的橄榄球游戏[57]。施行“电子化”战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团体,则有如下政策:
“组织密切关注计算领域的爱好,包括用数字集成电路装机,也包括在可编程计算器和微型计算机上开发计算程序和游戏程序……以此引导青年技术人员数量的增长,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作出贡献。”[58]
同期,亦有将“趣味编程”向全世界推广的理念。[59]
其次,是数字世界的创新。对以游戏作为素养启蒙的个体而言,创造是相当自然的过程:在重复键入多次游戏源代码的过程中,渐渐弄清每一行代码有何功用,再尝试小修小补,最终实现人生中“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程序”。[60]恰如马修·威尔斯(Matthew Wells)的观察:
“‘创造性计算’这一概念,至少部分地包括创造并开发小游戏……在创造性计算相关的内容中,游戏事实上占据了愈发显著的篇幅。”[61]
创造属于自己的程序的过程,时常伴随着令人难忘的“心流”体验:“我想对爱好者自己写游戏多说一点……你首先得有灵感,进入想写点什么的节奏,你的手不会离开键盘。这让人快乐,你不会无聊,你不会疲惫,你不知道时间的流逝。”[62]由此自然可以理解,为何计算机可以迅速在校园内激起“汹涌的创造力”。[63]
源于游戏的创新也早已远远超出了游戏本身:走出了“画板”、虚拟现实、操作系统,也有美学、文化、乃至“游戏”本体论层面,众多创造性的探索。[64]于是,在由易用到常用以后,还有从常用到善用。
05
游戏能成为算法治理的出路?

如上文所述,打开计算机这一物理意义上的“黑箱”,是游戏的历史意义之一;如今,我们正面对着另一个有待治理的算法“黑箱”。
游戏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游戏“驱散计算机的神秘感”的关键之一,即在于令个体自然地理解程序、创造程序。算法尽管可能相当复杂,但说到底依然是一道程序。
于是,游戏的三重意义均足以发挥治理作用:更丰富的交互,意味着更充分的解释算法的空间;对算法的接受,指向在算法社会中相当重要的“控制感”;数字素养的提升,在令个体对算法“知情”更易实现的同时,也为“利益攸关方参与”提供了更多选项。[65]
在这三重意义下,游戏都有相对成熟的实践。
其一,面对开发者制定的代码规则,除开简单的遵从或拒绝,用户早已形成富有创意的交互手段:既有对规则之社会意义的重新解释,也有对代码输入、输出的修改,还有对规则本身的编辑。以“故障艺术”为主题的游戏、花样迭出的修改器与已然成为众多游戏组成部分的游戏模组修改(常简称“MOD”),是三种交互手段各自的代表。[66]算法下的自主,因此不再是简单的0-1问题,而有了更多选项。
其二,利用“游戏化”设计,在保留个体控制感的同时、增强算法的引导或支配能力,已是出行平台等场景中常见的设计。[67]
其三,自发形成、稳定存续的MOD开发社区,可谓充分实现了算法治理的两项愿景:一方面,持续地、阶梯式地培养足以胜任开发工作的人才[68];另一方面,以富有意义与实效的方式,实际参与到代码规则的制定与增补中——“这很有趣味……代码规则的一切都是未知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去发现,如何将自己的想法,落实到代码规则里面。”[69]
结语
重新定位游戏:保护游戏权
数字文明下的“数字人权”[70]或“第四代人权”[71],日益成为显要论争命题[72]。不过,在将今日数字文明视为给定、进而证立或证否权利以前,思考“何以数字文明”,定当有所助益。
从交互变革、数字设备普及到数字素养建立,游戏在每一个环节都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现在,对数字治理中颇受瞩目的算法治理问题,游戏已然提出了多种可行的选项。
正因如此,数字文明的开端或兴盛,始终隐式或显式地依赖于对个体游戏权的保障:否定游戏的权利,一定意义上,也就否定了数字文明的基石;同时,如果说数字文明下存在任何基础性的权利,从文明本身进程出发,当中都应有游戏权的位置。此外,从国际竞争的功利主义角度而言,历史的经验,也倾向于对游戏权的保护。
数字文明下,游戏同样可以作为得力的治理工具。
如前文所述,电子游戏的开端之一,便是控制论思路指导下的计算机战棋;同时,对大型平台等私权力主体而言,游戏化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治理思路之一。从更加一般的角度出发,如果期待在数字治理秩序中保留一定的自发性或创造性,并提供有意义的个体参与,最终能够长期存续的实践方案,很可能与游戏方面的探索所得同构。
由此,游戏既是基础性权利,又是数字时代权力运行的可行模式。
从有关权力的另一角度出发,就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关“游戏”与“严肃性”间的、具有长久影响的辩论而言,相比后者令游戏受制于严肃性的论点,前者视游戏具有超越性的论点,距离或许难以折返的“(数字)紧急状态”,很可能要更远一些。![]()
参考文献



